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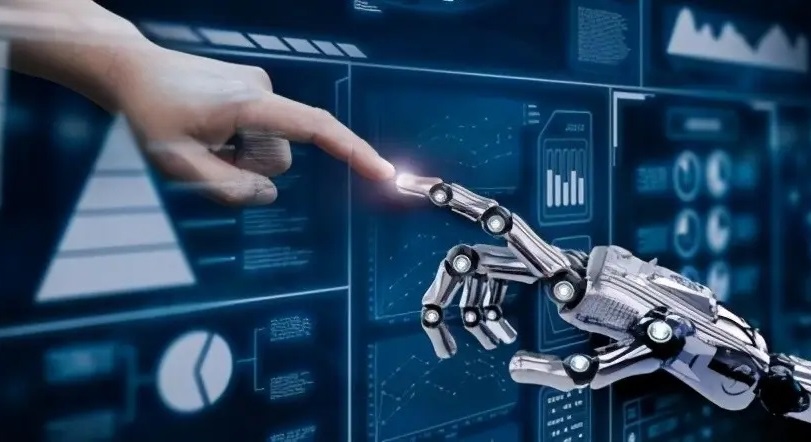
编者语 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最新应用在多大程度上预示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本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批判性评估,挑战了无情的技术决定论,并重新构建了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方法中涉及的问题。以主权和话语权为中介,聚焦于技术创新的经济、政治和历史动态,及其对就业和经济重组的影响。确定了转型主义立场的一系列认识论和经验问题,并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即强调围绕当代和未来趋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敬请阅读。
01 介绍性评论
对基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的新技术的社会动态和后果的关注已成为学术、专业、公共政策和商业话语的一个主要主题。在社会学领域,诸多学者对新的人机交互模式、智能系统动态技术发展等进行了论述,并纳入到技术与人类进步活动的框架范畴中研究。本文并不在于构建庞大的分析理论,二是专注于对商业和政策导向的辩论进行批判性评估,这些辩论假设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将导致由技术创新过程引起的前所未有的就业社会变革。
当澳洲经济发展委员会(Committee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ustralia,CEDA)在2015年年中发布其关于澳大利亚未来劳动力的报告时,其对机器人技术影响下的高技术工种脆弱性的预测,反映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范围的拓展对技术和非技术从业者的破坏性影响。美国、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就业脆弱性规模总体上约为35-50%。这种就业破坏在多大程度上会伴随着新的积极机会,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造成彻底的负面影响,仍有待商榷。部分评论家视之为机器剥夺人类工作的世界末日,而智能化也意味着新的权力结构的开端。这种根本性的变革引起了当代劳工组织和社会活动家们的关注,旨在扭转国民收入中用于劳动的份额下降的趋势(Haldane,2015),并加强民主对企业权力的渗透。他们还提出了关于机器人在人际环境中使用的伦理和法律影响的难题。
相比之下,在许多商业话语中,激烈的技术变革被归入“创造性颠覆”的规范之下。自“颠覆”这个概念带入到技术和组织创新中,就被视为创新的助产士。但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创新的作用或者影响是有限的,不应当过分乐观。
对于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拓展了人们创新能力。可以说第四次工业革命整合了前三次工业革命对人类有益的变革(Klaus Schwab,2016)。但根本性的技术变革阶段是偶发的和不连续的。
而关于技术变革的乐观言论多集中在“时代不同了”的论点上。这一论点认为人与机器之间关系的根本变化意味着人类适应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该论点来自于生命的未来研究所发布的文件“强大而有益的人工智能”(Russellet al., 2015)。文件认为高新技术的应用能够用来解决技术导致的社会问题,以使社会易于接受进一步的技术干预的方式来构建这些问题。该文件所展现的技术决定论否定了新技术的应用与社会环境以及“技术”、“机器”、“人类行为者”和“智能”等构建的错综复杂的话语和内在联系。这就需要更深入探讨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与社会、政治背景以及技术传播相互影响。
我们的论点是:首先,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所声称的各种变革性影响不能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必要的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一立场建设在多学科的立场之上,借鉴了如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观点,是对预测变革性技术革命的言论的一种质疑,而不是完全反对。其次,对于根本性的技术变革是否会对经济生活和社会凝聚力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我们的立场是一种规范性的开放态度。因而本文的潜在主题是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不是技术乌托邦主义或世界末日预测。
02 什么是新的?有什么不同吗?
试图理解技术创新和社会变革的过程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分析问题侧重于变化的性质及其原因;规范性问题审查根据各种标准判断变化具有积极和消极特征的程度。
在当代辩论中可以确定两个主要的分析立场。首先,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只是一系列重大但不具有变革性的技术变革中的最新成果。它们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技术工人失业,但它们并不代表经济组织的重大新旧分水岭,也不代表对社会生活的新规范挑战。第二则认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代表了无与伦比的转型变革。
(一)没有实质改变
经济学家戈登(Gordon,2014)和考恩(Cowen,2011)最近强势提出“无实际变化”的立场。他们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远远无法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恶化,其作用也就无法与前几次工业革命相提并论。这一观点对技术促进转型论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一方面在于应用任何一种创新的收益递减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在于信息技术核心不断增长的假设,在摩尔定律中象征性地预测计算能力每两年翻一番。
评估“无实际变化”论点的一种方法是考虑新技术(包括机器人技术)的纵向证据,以确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趋势。格雷茨(Graetz)和迈克尔斯(Michaels)(2015),使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IFR)生成的历史数据集研究机器人技术对生产力和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头五年,随着机器人成本的显著下降,在运输、化工和金属加工等行业的机器人技术应用提高了生产力,即使存在使用折旧和再供应等问题,机器人的应用也带来了一些对就业的不利影响。上述结论信度是有限的。它的数据仅针对工业机器人,而新一代能够主动收集、解释和学习的大数据机器人技术不在此列。
考虑到新技术只有成为通用平台系统后才能产生革命性影响,因而与蒸汽或电力的应用比较也应持谨慎态度。那么,机器人/人工智能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这样一个新平台?
表面上看,“智能机器”的大规模应用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显著影响,例如:辅助收费、照顾婴儿、传递信息、自动驾驶等等。但是这样的应用是避免与处于“我们”变革体验核心的“我们”有任何接触,以及对智能机器技术发展和再生产中的不平等视而不见。它绕过了人类学的见解(MacKenzie,1998:6),即技术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意义。
而在新技术应用拓展过程中,有一个关键问题:人工智能是否能替代人类智能?机器做不到什么?答案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二)非常真实的变革
坚持第一种立场的人毕竟是少数派,大多数仍认为技术和社会正处于彻底变革的过程中。无论是乐观或悲观,他们都认为彻底的技术变革是真实的为社会带来全新的影响和挑战。
实际上,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早已促使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200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富裕经济体对非技术工作的需求减少,而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回报增加。而于2014和2015年的一系列研究表明,一系列新技术的应用将改变专家的工作,提出专家和机器人将可以相互补充,配合完成高难度工作。但是这些研究忽视了智能机器的应用和普及率存在的限制或不确定性。
虽然有大量证据表明服务业就业在所涉及的技能范围内发生了变化,但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存在全行业普遍威胁。例如,单一重复劳动的职业被替代性可能更高,相反,则被替代性更低。因此转型是真实的,但是危机被夸大了。
那么新技术的应用与就业等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本文认为取决于人们认为就业转型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其中一种观点是虽然技术转型通常会侵蚀或破坏一些职业,但通过转型过程也会创造新的职业(Mokyr et al.,2015)。新技术的应用提高了本部门的生产力也为开发新流程和服务创造了机会,因而随着生产力和实际收入的增加,不断拓张的经济对劳动力的总需求通常也会增加(Autor,2015)。例如,机器人技术的应用,反而可以拓展包括机器人维护和维修等的新职业。
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也关注引起人们对采用或拒绝技术创新决策背后的企业战略。新技术的应用存在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斯宾塞(Spencer,2016)认为技术变革通常被视为一种中性的背景力量,而不是与生产政治和权力结构相关的过程。依据马克思理论,大多数技术出现在不平等的情况下,且技术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资本的推动。关键问题涉及谁控制数字技术、机器人和基于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以及为什么对这些领域的政治监管通常很薄弱。除了新技术应用的复杂性外,公民和消费者的文化偏好也将推动复杂性。现有研究在对机器人文化的态度以及是否因年龄和民族文化而差异,但仍有巨大的缺失。仅仅说明可能避免一定程度的转型性失业。
本文论点认同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因素中寻求解释技术和技术系统的发展、部署和传播时的关键作用。这里之所以强调“非技术性”并不是完全否认新技术对社会的塑造作用。根据既有研究提出两大类技术或系统发挥权力的情况。第一种是通过技术支持、深化或拓展现有社会关系安排,以牺牲其他社会群体为代价为部分社会群体提供特权。第二种是关于技术或系统的内在政治性质。温纳(Winner,1980)提出并区分了强变体和弱变体。强变体指的是作为其运行环境的特定技术系统需要创建和维护一组特定的社会条件,机器人或人工智能作为技术的载体将人类和技术相分离。弱变体则是指给定的技术“适合”特定的社会安排,或与特定的社会安排兼容,技术的存在为人类的行动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补充和可能性以减少意外因素的发生,即能动的协调人与技术的关系。这种人类与智能机器动态协调、协同发展的观点具有相当的证据支持,如作为工艺和艺术实验再培训的催化剂。在亚瑟(Arthur,2009)的经济-技术协同进化的复杂系统理论模型,技术的应用、问题和经济需求的相互互动将推动社会变革至更高水平。
当前论点中能够最有力反驳“没有真正变化”立场的是,一连串相互关联的技术变革正在接近转型的起飞点,通用平台将从这里出现。当下,随着数据存储、计算能力和无线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机器人或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入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机交互和“深度学习”似乎将彻底改变人类和机器的关系。当下出现的新情况是机器人或人工智能正向曾对它们抵抗性较大的行业拓展。理解技术变革所涉及的关键转型平台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物联网”的概念(Greengard,2015)。通过网络将数据实现实时的相互通讯,将人类活动抽象为万亿节点的关系网络,缩短了人与人和人机交互,从而彻底改变人类生活。
综上,本文已经阐述这是一种彻底变革的论点,但确实存在某些问题和限制。其一是历史观点,即技术变革对就业和社会的影响存在周期性循环,变革确实发生了,但是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彻底。其二是缺乏明确的话语力量展示清晰明确的未来图景。鉴于这些考虑,我们勾勒出第三种应对当代技术变革的替代分析方法,该方法承认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采用怀疑的社会学方法而不是预言的话语模式。
(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一种社会学视角
对未来趋势的分析总是存在主要的认识论(Adam,2006)和本体论(Selin,2008)局限性。对亚当(Adam)来说,直接了解未来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准确的预测未来,因而当面对技术决定论者无处不在的修辞确定性时,认识论上的谨慎就显得更加必要了。对于塞林(Selin)来说“未来的本体论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不可能知道未来,因为我们一直在创造和积极地再创造多个未来,其中任何一个可能(也可能不会)实际出现”(2008:1888)。因而完全有必要批判性地评估关于技术变革的合法化话语的范围——无论是被视为不可避免的和有益的,还是危险的和反常的。因为关于技术变革的叙事不仅位于技术创新和传播之上,而且有助于构成和指导或重新指导变革本身。
一项开创性研究中,保罗·杜里什(Paul Dourish)和吉纳维芙·贝尔(GenevieveBell)2011年的研究描述了普适计算先驱们创造的叙事如何为非技术手中提供他们所设想的人机交互的新现实,并提供了一种可以实现的研究计划。当现在诸多普适计算创新深入影响我们的生活,但与研究者所描述的相去甚远。
因而这种第三选择的视角就是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置于分析的中心。既有的经验很难回答新技术应用的当前状态,如是否有效?能否克服障碍等等。但在经济史中技术传播可以有效纳入分析,即技术传播的范围和方式,这就将社会、经济、政治等要素代入技术和社会变革之中。一项关于1999年至2010年意大利手术机器人扩散的非常重要的纵向案例研究提供了对技术变革范围和限制的详细社会科学解释(Compagni,2015)。该研究同时关注组织和社会行动者。关键问题是为什么在一系列医院和地区环境中的外科医生、管理人员和卫生政策制定者要么是早期采用者、后来的采用者,要么选择不采用此类技术。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得出,技术创新的采用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无情的。技术传播也不是由与创新相关的明确的单一理性工程效率决定的。有时还有其他合理的成本收益计算在起作用。简言之,在一个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过程中,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影响都在起作用。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纵向和定性研究来综合说明技术传播的局限性。但现有论据仍可说明“时代不同了”的论点仍然存在严重的认识论、理论和经验问题。出于这个原因,该领域的未来研究将比专注于激进转变的单一假设更好地开发更广泛的研究计划。
03 总结
“这个时代”与历史上发生的既不同又相似。相似的是,技术变革具有变革潜力以及不确定性和局限性。不同在于商业和政策制定的修辞动力落后于技术决定论者。本文中,认为社会科学和社会学观点提供了确保对权力和不确定性敏感的确定性较低的分析方法的方法。虽然我们不直接解决规范问题,但这里勾勒的第三个分析视角具有规范意义,因为它提出了替代未来的可能性,机器人/增强型人工智能论文可以据此进行评估。除了激进变革论点的反乌托邦或乌托邦链之外,未来的可能性允许根据多种规范观点阐明和评估关于未来趋势的一系列相互竞争的假设。如果要围绕新技术出现协商民主的话语,这种做法至关重要。